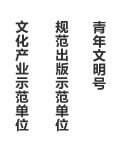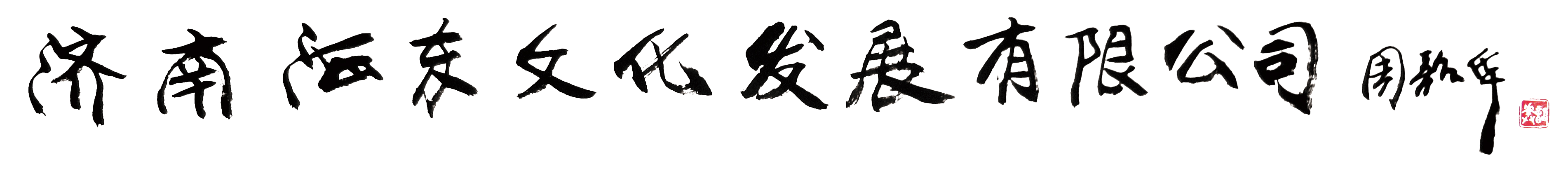泉城忆
石英
回忆,仅仅是回忆吗?仅仅是过往某种生活影象的复制吗?
不,它有着本能的筛选。有的沉淀,有的浮涌;不忘旧事,推出新意;固然也有苦涩,但大都与美好的感受相连。
泉城就是这样常引起我深深的怀念。
五十年代,我在济南度过了难忘的七年时光。从当时国家形势说,是刚刚解放百废俱兴的经济恢复阶段;从个人来说,是由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转折时期。一情一景、一人一事、一鳞一爪至今想来都历历在目。但我偏爱记叙二三件小事。怪吗?
大观园的灯光
我们机要部门当时是实行二人以上通行制的。现在看来也许很别扭,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怨尤。尽管上街闲逛的机会不多,却唯对大观园非常熟悉,尤其是园内那通夜不灭的灯光,至今还溶在我的心底。
我们日夜都在工作,有时晚饭后干了几个小时,电报的势头稍有松缓,只要我们这些“大孩子”中的长者老徐大胆提议,我们三五个人便异口同声地响应,于是便穿破夜色走出军区机关的大门。
那时的大观园,一进南门口就灯火辉煌,琳琅满目,橘子象身披金甲的将军把守在大门两侧,灿黄灿黄的,反映着灯光。只不过那时一般人的购买力并不怎么强,所以总是垛得高高的。进得门去,两边全是各色各样的店铺,八九点了,还在照常买卖。我没有细数那些店铺(也数不过来),大约要以数百计吧。
从南门说,左首是大观电影院,右首是大众剧场。我们那时看电影多半是在大观影院,不仅因为路近,也因为它在大观园里,有一种格外热烈的氛围,这是我们不言而喻的心理。同时因为这里灯火辉煌,对于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来说,行动也比较安全。
在大观园,有时我们看完电影,如果肚子饿得紧,还可在夜宵小吃店吃碗“米粉”,几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个别星期天工作不多,我偶而也和小伙伴一起到这里的大众剧场看场京戏,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三打祝家庄》。看完了戏,还可就便在大观园后身小饺子铺里吃盘“扁食”或去大众剧场后面的“狗不理包子铺”吃包子。
大观园的灯光映衬着五十年代初期的社会面貌,也反映着我们热血少年的纯洁心地。它留给人们的光色是美好的,虽然也许过于纯朴,然而非常充实。
工作不分昼夜
进入五十年代的前三年,正是轰轰烈烈的土改、镇反、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高潮期,党、政、军、公安系统的电报沓来纷去。每天,从一睁眼睛干上去,一直到深夜;刚刚把一轮工作处理完毕,回到宿舍,一沾床铺就进入睡乡;也许只睡了一两小时甚或半小时,就有人来拍脑袋了:“喂,起来吧,来(电)报了!”
这第二轮工作,一般都要干到朝阳临窗、灯火倏熄之时,但往往又接上了次日的电报洪流,因此,竟常常忘记了准确的日子,只有在填写收发报时间时,才蓦地问起:“今天是几号?几点了?”
可是,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、应当的,是党的需要,人民的需要,心底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便由此而生。
济南那几年冬天忒冷,雪下得既频且厚,我们宿舍那个小小的天井院经常被装点成银色的“小盒”。屋子里既没有炉子,更谈不上暖气,加上夜里随时都准备通讯员来送电报,门经常不关。风雪毫无阻挡叫啸着往里硬灌,脸盆里的水都瑟缩着,变成了冰疙瘩。我们常常从睡梦中被冻醒了。我有个爱转腿肚子的毛病,一抽了筋半天不能复原,勉强扭过来还有后遗症。也难怪,薄板床上只有一个草褥子,上面铺一层床单,发的一条蓝粗布面的被子又短又窄,两边掖不住,顾头顾不了脚。
我们的刘股长有时来查铺,一抄铺底下,不由得皱起浓眉,摇摇头说:“这家伙,真能吃苦!”
这就够了,我听了已经得到很大安慰:领导同志给了这样的评价就是一种褒奖,我从没想再要求什么。
大约是一九五一年早春,镇反运动刚刚开展,一个内好在晚会上刺杀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同志。我当时正担任惠民台的通报任务,深夜,张科长亲自把我唤醒,交给我一份上级“指人译”的电报稿,要我立时发往惠民地委和军分区,通知在几个钟头前发生的事件及对有关事项的布置。
我马上奔向办公室,以最快的速度把任务完成了。“指人译”,通常是要由科处长亲自译的,而领导上交付给我了,我感到这是组织上对我最大的信任。看了电报的内容,我心中交织着对内奸叛徒的忿恨,对首长被害的痛惜。我忘记了疲劳,不分昼夜地工作。
这就是那个年代里年轻战士的是非观和荣辱观。它是真诚的。
珍珠泉微波
一九五二年九月,在珍珠泉召开了山东省团代表大会。在会上,表彰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模范团员。我作为机关代表,参加了大会。
在那些日子里,我心里一直觉得很不安。大会间隙,我倚立在栏杆上,俯视着珍珠泉中那汩汩上涌的永不断线的珠泡,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这中间的一个水珠而已,充其量只是闪露出一点微光。重要的是不应满足于做这瞬息即逝的水泡,而应做一颗坚实的真珠,即使沉落下去,也不会黯然失色。
大会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上,我便明显感到身体不大舒服,低烧、疲惫,以至吐血了。我们的孙科长发现我气色不对,便关心地问我:“你怎么啦?腮那么红?”
“没什么,我……”我吞吞吐吐地,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,但我不愿让领导上知道我吐血了。我朦胧知道:咯血,是肺病的象征,如果暴露了病情,领导上肯定要叫我去休养,我怎能中途退下阵来呢?
然而,X光的显影是不容置辩的,我被判定患了浸润性肺结核,医生的珍断书是严肃的:全休三个月,复查。
也只好如此。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时,孙科长追上了我,把一份空白的入党志愿书递给了我,要我马上填表。我愣住了,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!我庆幸自己并不空虚,我在继续填写自己的历史;我没有走下战场,而是作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名新兵,惊喜而惶悚地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在短期的养病期间,我也并未完全闲着。我读了不少政治、历史和文学书籍。我发现自己在中断数年之后,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也未减弱。没想到养病成了我日后踏上文学道路的奠基阶段。
我试探地拿起了也算是文学的笔……
我对泉城的回忆,是在重温一支心底的歌。它的音符是青春与赤诚、奋发与献身!
(选自《海鸥》一九八三年十二期)
石英,当代作家,原名王恒基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生,山东黄县人。五十年代曾在济南工作。随后毕业于南开大学,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和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。从六十年代至今已出版许多部作品,其中有长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和传记文学等。现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兼《散文》月刊主编。